“关系”会影响经济效率吗?
“关系”,作为一个词汇,是如此富有中国特色,诸如relation、relationship、connection、ties之类,都难以曲尽其妙。以至于在英文世界里,也只能特别发明一个单词“Guanxi”来和它对应——实际上这个词早已登堂入室,进入牛津英语大词典了。
和“腐败”一样,“关系”对很多人来说有点儿像长沙火宫殿的名小吃臭豆腐: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。在正式场合,“关系”这个词并不讨喜,尤其是前面再加上一个字:“搞”。当人们说起某人热衷于“搞关系”、某个单位“搞关系”成风之类,大概都会伴之以鄙夷的神情。不过一旦自己身临其境,不少人的第一反应还是:能不能托点儿关系?
翻开现在高中生必读的四大名著,毫不夸张地说,每一部讲述的都是以血缘或者准血缘为基础的“关系”世界里的故事:打草鞋的要起事,先得强调自己是“刘皇叔”,这是和大汉朝廷攀关系;桃园三结义,这是关系的升级,从非血缘的朋友升级为准血缘的拜把子兄弟;梁山泊聚义厅的结拜,孙悟空在各路神仙处的面子,刘姥姥托周瑞家的进荣国府……也处处都是关系。
关系和稀缺资源的配置息息相关。如果不是曹腾的养子,曹嵩就没法继承曹腾的侯爵,曹操也未必有机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中国的中古史就得改写。如果没有众多关系加持,宋江就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到“浔阳楼”喝酒题反诗,而只能老老实实在江州的监狱里服刑。如果不是贾母的外孙女,林妹妹根本没机会进贾府,更不可能和宝哥哥演绎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反过来,但凡有老鼠精、玉兔精一半的关系,白骨精就不会死在孙猴子的金箍棒下。
时至今日,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当中,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照样不容忽视。在美国的人才市场上,熟悉情况的导师或者同行专家的推荐信,对于博士生就业仍然至关重要。墨西哥籍的劳动者在美国劳动市场找工作,同乡等熟人网络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。
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·格兰诺维特在《找工作: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》一书中的意见,人们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两种:“弱纽带”与“强纽带”。所谓弱纽带,他界定为一年见面一次的联系,这近似于人们常说的“泛泛之交”。而强纽带则意味着更加紧密的互动,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庭或家族纽带,导师和学生之间紧密的师生关系,交往频繁的朋友、同乡关系等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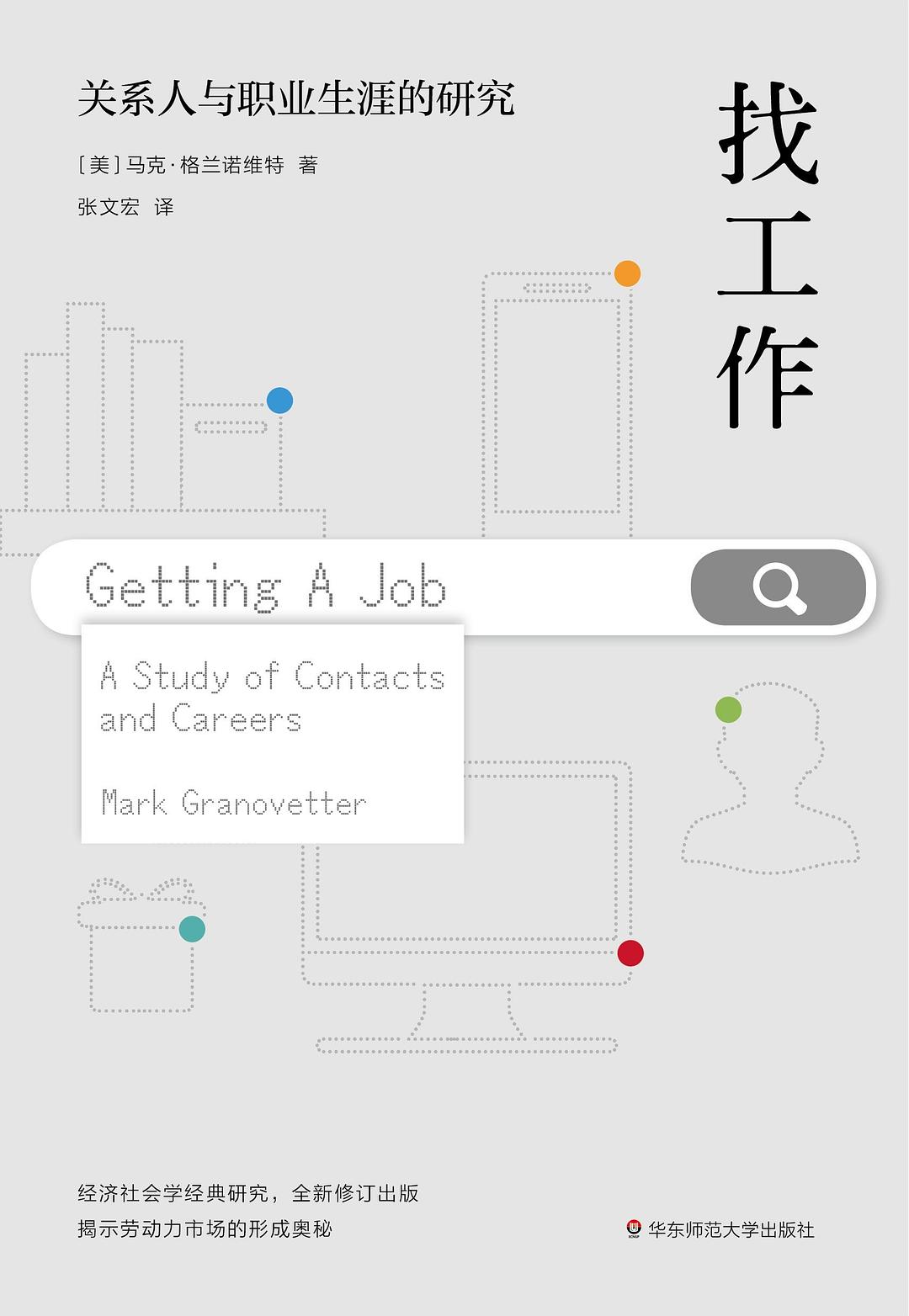
《找工作: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》,马克·格兰诺维特 著,张文宏 译,薄荷实验|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版
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表明,对于个人而言,弱纽带的经济价值要高于强联系。他的解释是,强纽带构成的网络虽然信息传递性更强,但也更加封闭,即强纽带的个体之间共享着高度重合的信息,因此可以通过交往所获得的新知识是很有限的,而弱纽带则是虽然更松散、信息传递性更差,但同时也更开放的网络,个体之间则可以通过面对面沟通,获得更多完全不同的新知识来源,从而发现更多的经济机会。
显而易见,本文所讨论的“关系”,更接近的不是格兰诺维特研究中的弱联系,而是强联系。
这种强联系的特点,一是成员之间相互熟悉程度比较高,二是联系人规模比较小,三是交往频率比较高,四是稳定、可持续。与这些特点相适应,人们之间的强联系通常建立在血缘、地缘、共同的价值观、长期的合作等的基础之上。
上述特点意味着,“关系”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机制,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,它是基于“身份”的,或者说,是高度“人格化”的。
换言之,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“关系”决定,也就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取决于他在“关系”网络中的身份。他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谁,他爸爸是谁,妈妈是谁,爷爷奶奶是谁,外公外婆是谁,和谁结婚,做谁的学生,和谁交朋友,如此等等。
理论上,这种基于“身份”的关系,对应的很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状态。
原因很简单:以身份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,意味着每个成员能够深度参与的合作网络不可能太大,基本上就是他所熟悉的人构成的强纽带网络。虽然强纽带网络成员内部的信息交流成本低,成员之间信任程度高,但不同的强纽带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本却非常高,相互信任程度也很低。
于是,整个社会就被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小“圈子”,也就形成一道道无形的壁垒。这些壁垒阻碍着不同圈子之间的交易,从而形成并不断强化着对交易范围扩张和社会分工深化的桎梏。
这种低效率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:“裙带关系”盛行和要素流动受阻。
首先,强纽带网络内部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种裙带关系。这是因为,熟人之间因为交往密切而有着更强的亲近感,加上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,而熟人之间因为“知根知底”有着更高的信任感,所以人们倾向于将经济机会留给“圈子”内的“自己人”,而不是能力更强或者资源使用效率更高的“外人”。
其次,强纽带网络必然阻碍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或者跨行业的流动。在“圈子”文化盛行的环境下,个体离开原有“圈子”就意味着失去“圈子”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安全感,而又很难再进入新的“圈子”。换言之,人们很容易被禁锢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者行业领域之内。
人类为什么能够从低效率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中逃离出来,进入持续内生增长的现代文明?一个常见的解释是:工业革命。
经济史学家克拉克(Clark)说,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,那就是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;其他事件可能也有趣,但都不关键。
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?很多人归因于瓦特改良蒸汽机等一系列技术发明。但实际上这一系列技术发明本身只是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,而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。
追根溯源,工业革命的发生,离不开制度的深刻变革,其中最重要的,就是产权制度的变革,以及随之而来的契约和法制社会的兴起。产权制度变革最核心的特征,就是人们的权利,或者说人们的行动空间,从基于“人格”或者说“身份”,转向了基于“物”或者说“财产”。
现在民法典里关于财产权利的法律,就叫做“物权法”。
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在于,人们的经济活动摆脱了以身份为基础的强纽带网络的束缚,可以和同样拥有以“物”为基础的权利的陌生人,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易。这样一来,分工和合作网络就突破了熟人社会的小圈子,扩展到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现在我们日常消费的商品,无论手机还是咖啡,可以说都是全球化的产物,即全球范围内陌生人相互合作的成果——尽管这些合作者不仅相互一无所知,而且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,甚至可能相互仇视!
这个转换也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。
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,所以梅因在《古代法》里的那句名言才广为传诵:“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,到此为止,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”。
于是,我们几乎可以马上得出结论:基于身份的“关系”网络,对于提升经济效率而言,是不利的;一个社会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,基于身份的“关系”必然逐步消退,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。
但是,在过去四十余年,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同时,以“强纽带”为基础、以人格化交易为基本特征的“关系”网络,却仍然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并对经济运行的绩效产生着复杂而重要的影响。
(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、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)
